-
+1
-
陈寅恪为什么要研究杨贵妃的初夜给了谁?
2014年最具有话题性的电视剧,非《武媚娘传奇》莫属,从这点上来说,这部剧对得起“传奇”二字。这里面,除了广电总局功不可没外,编剧与有荣焉。如果说96集的“武则天传记”,除了到60集观众终于等到唐太宗驾崩,是编剧带给我们的一大“惊喜”外,那么到了后半段,剧中出现的史学巨擘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说,则让历史爱好者激动不已。

武则天和“关陇集团”
“关陇集团”这个名儿,是陈寅恪给起的,又叫关陇六镇集团、六镇胡汉关陇集团或武川镇军阀。最初是清人赵翼看到北周、隋、唐的创业者都在武川镇做过土豪,认定那里有王气。(《廿二史札记》卷十五)

这个王气之地现在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武川县,在北魏时期是不同于州、郡等普通行政区域的特别军事区——“六镇”中的一个。安徽凤阳出了一个朱元璋就名闻天下,武川镇先后出了北周宇文泰、隋文帝杨坚父亲杨忠、唐高祖李渊祖父李虎,连着三代皇室,依然默默无闻,只能怪寅恪老先生的“关陇集团”名头太响,掩盖了武川镇的光芒。

关陇一带地图。

所谓“关陇”,是指渭水盆地一带的关中地区,以及李唐给自己脸上贴金的陇西成纪等地。赵翼说武川镇有王气,陈寅恪看不下去了,什么王气啊,不科学。陈寅恪说,历史怎么会是英雄创造的呢,组织才有力量。这个组织就是由北魏六镇的鲜卑贵族和关陇地区的京兆韦缜、河东柳泽、太原郭彦、武功苏椿、河内司马裔、敦煌令狐整等豪族所组成,所以陈寅恪命名为“关陇集团”。
集团的特点除了有钱有权外,就是关系比较复杂,真正做到了胡汉一家亲。比如,杨坚和宇文泰儿子北周明帝宇文毓是连襟,杨坚又是北周宣帝宇文赟的老丈人,而李渊的父亲李丙和杨坚是连襟,李渊的儿子李世民又是杨坚的孙女婿。有点乱,这么说吧,宇文毓、李丙、杨坚都是北周柱国独孤信的女婿,杨坚是李渊的小姨夫,杨坚又是北周末代皇帝静帝的外公,杨广是李渊的表哥,宇文泰是李世民的曾外祖,更乱了。嗯,这就对了。
当然光看到乱就看不到问题本质,北周、隋、唐三代远不是轮流坐庄那么简单。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陈老说的不是生物学上的“杂交优势”,而是胡族文化给已经渐趋凝固的汉族文化带来了一阵新风,所以才有了交融开放的大唐,以及供总局可剪的“武大头”。
陈寅恪认为,等到武则天登场,借山东豪族打击关陇门阀,这个日渐腐败传统集团才被彻底破坏。原因就是武则天出身不好,本家不是组织成员。但史学界另外两个大佬岑仲勉和黄永年表示,万万不能同意。岑仲勉说,武则天怎么不是根正苗红,她爹武士彟是最早跟李渊闹革命的一部分人,难道武则天连本家也要打击?黄永年则说,你看看隋文帝朝的“四贵”、隋炀帝朝的“五贵”、越王杨侗时的“七贵”的出身和经历,关陇集团啊,嘿嘿,早就解体了。
所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孙英刚指出,武则天的母亲是隋杨皇室,她本人也对自己西北贵族尤其是隋杨皇室的出身有着强烈的认同,和唐高宗李治联手打击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并非出于什么政党斗争,而完全是对当权派的夺权,所用之人李勣、李义府等也不是出于郡望考虑,而是高宗的王府和东宫旧部这层关系。孙英刚认为,当时,高宗在长孙无忌等“大老虎”的裹挟下,根本无法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和作为君主的权威,所能依赖的只有当年教自己读书、陪自己读书的老伙伴、小伙伴。
但是不管是反驳、修正,还是推翻,陈寅恪提出的“关陇集团”说,是后来治隋唐史者几乎无法绕过的命题。陈先生讨论“关陇集团”,是他一贯对“种族与文化”的执着,所以他也会研究杨贵妃入宫前是不是处女这样在当时招致很多非议的命题,也会在晚年倾尽全力研究一个秦淮名妓。
杨贵妃的初夜给了谁

称陈寅恪为国学大师,恐怕鲜有不心悦诚服的,当然他的学问也不仅限于国学。这样一位大师,竟然在课堂上讲“杨贵妃入宫时是否是处女”这样一个课题,自然让“正经”的中国人感到不适,大骂其无聊、龌蹉。
但只要了解陈寅恪一贯的史学思想,就会明白他关心的根本不是这个胖女人初夜到底给了谁,而是通过这一问题观察唐代的婚姻制度,胡汉混血带来的贞洁观念转变,乃至李唐王朝的血统、风气和政治演变。如果一个皇帝都可以接受非处女,我等屁民还有什么可纠结的。
那陈寅恪是如何考证的呢?杨贵妃原先嫁的是唐玄宗的第18个儿子寿王李瑁,唐玄宗娶的是比他小34岁的儿媳。清初学者朱彝尊细致考证了杨贵妃入宫始末,认为虽有寿王册封杨玉环为妃一事,但是还没来得及与寿王那啥,就转入道观清修,随后被唐玄宗纳入宫中,其时还是冰清玉洁。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杨氏入宫,至早亦必在开元二十六年正月二日。其间相隔至少已越两岁,岂有距离如是长久,既已请期而不亲迎同牢乎?由此观之,朱氏‘妃以处子入宫似得其实’之论,殊不可信从也。”也就是说杨玉环在入宫之前,已与寿王订亲至少两年,并且按照唐代亲王娶亲的礼仪,迎亲当天即“同牢”(同房),让寿王做柳下惠显然有点困难。
季羡林对于陈寅恪这个选题和论证很是钦佩,他在《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一文中写道:“寅恪先生考证不避琐细,但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小中见大,其中往往含着极大的问题。比如,他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这个问题确极猥琐,不登大雅之堂。无怪一个学者说: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焉知寅恪先先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寅恪先生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

除了唐代两位重量级女性,陈寅恪先生晚年时期,还特别研究过明清两位才女柳如是和陈端生。1954年,陈寅恪动笔写柳如是时,已经64岁了,而且双目失明,最后花了九到十年时间写下了《柳如是别传》。为何在又老又盲的情况下,陈寅恪要穷晚年全力写一个秦淮河畔的妓女呢?有很多学者认为,陈老是想借着这部书发泄愤懑。虽然当时没有微博,没有朋友圈,可是要发泄还是有很多渠道的,何必费这么大劲拐弯抹角写一部85万字的妓女别传?
所以中山大学蔡鸿生教授认为,“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痕”,正是源自陈寅恪先生的文化使命感,是陈先生在卧榻沉思中追寻那种他唯恐失落的民族精神,自觉地承担起华夏文化的托命。
这正和陈寅恪一贯强调的“种族与文化”相印证,也和陈寅恪的身世和经历相联系。陈寅恪曾有诗曰“欲将心事寄闲言”,所以他以本是闲言的钱柳之事作为寄托,写了一部“心史”。除了柳如是,晚年陈寅恪还写了《论再生缘》,写清代女诗人陈端生,也可以算是历史学外的“闲言”。无论是《柳如是别传》,还是《论再生缘》,其实都是在“世变”中写“世变”,把身世感与历史感糅成一团。当然,正像余英时所言,其中的“兴亡遗恨”和“气节生死观”才是主旨,个人身世感怀倒在其次。
另外,陈寅恪研究柳如是也算是预时代之流。当时,柳如是研究是清末民初最前沿的课题。与陈寅恪同时代的大学者都在关注着这一课题研究的进展情况。王国维先生就曾在当时的《盛京时报》上发表过文章,提到了明清禁书中的柳如是。罗振玉也在其著作中提到了柳如是的研究。如此与时俱进的课题,陈寅恪参与其中也是情理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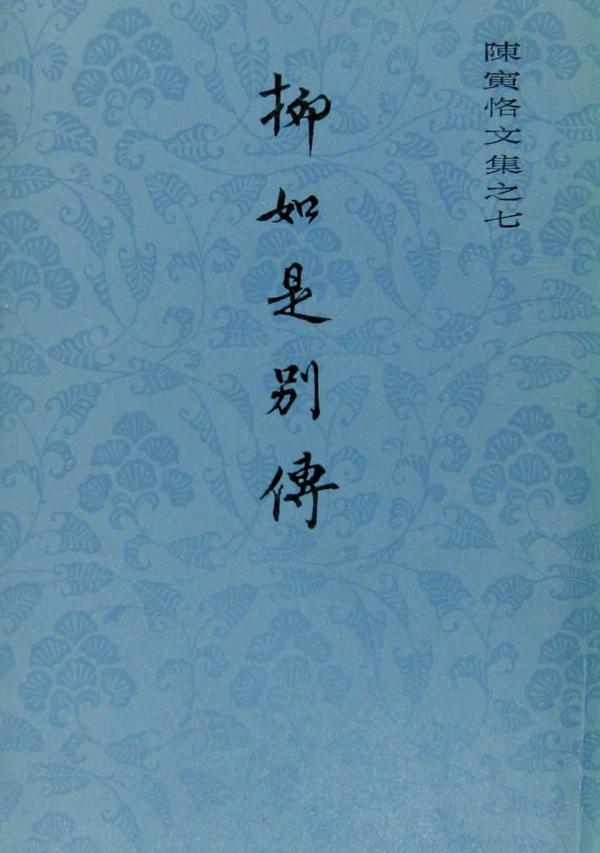
延伸阅读:
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岑仲勉:《隋唐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黄永年:《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