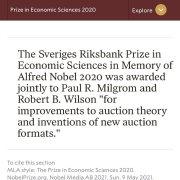先上结论:李昌镐是现代围棋史上仅次于吴清源的伟大棋手。
以下从三个方面说明:一是战绩,二是开创了一种很需要功力的特别的赢棋方式,三是对开局的下法有创新。
首先,就战绩而言,从1996-2006,几乎有十年时间,李昌镐一直都是高高在上,为人仰望。偶尔状态波动一下,人们奔走相告,但过两天他又回来了。
正是因此,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棋手都对李昌镐十分钦佩。 http://www. weiqitv.com/index/video _play?videoId=53c744f09874f0e76a8b461f 看围棋TV孟泰龄对珠钢杯李昌镐对孔杰一局的讲解,梦梦简直是化身为了李昌镐的“脑残粉”。李昌镐被棋手如此崇拜,我对此很能够理解,正如彭荃在围棋TV讲棋时多次说的,李昌镐的对手总是很困惑:我也没下什么坏棋,似乎还占了些便宜,怎么下着下着就不够了,并且还不是差一点,而是差很多?对李昌镐和曹薰铉战绩都很差的赵治勋在自述中说,输给曹薰铉自己服气,但实在没看出来李昌镐强在哪里,大家都说计算准和官子强,但这两点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一定还有其他的东西。现在当然我们知道李昌镐的强大来自于精准的判断和对全局的掌控。时越在围棋TV讲棋时说,虽然一般爱好者可能觉得李昌镐的棋不好看,但他们专业棋手十分佩服李昌镐对全局的掌控,确实非常强。这就是第二点要说的,李昌镐的赢棋方式很特别。
战绩和赢棋方式之外,第三点要说的是李昌镐对开局下法的创新。总是有很多人说李昌镐保守,没什么创新。这些人想必是被李昌镐的棋风误导了。棋风稳健和开局保守是两回事。回到90年代,当时《围棋天地》等围棋杂志上经常刊登韩国的新变化。而所谓韩国流定式基本上都和曹李师徒有关。
八十年代韩国兴起了围棋热,又碰上经济高速增长,因此很多企业赞助围棋。尽管韩国的比赛很多都不像日本七大头衔战那样持久,经常停办,但马上又有新的比赛取而代之,所以同时间存在的比赛始终很多,这也造就了韩国顶尖棋手惊人的对局量。训练量的提升必然带来研究水平的提升,韩国棋手不满足于已有的日本理论,而是对各种老变化重新研究,重新评价,并探讨新的下法,所谓韩国流呼之欲出。后来中国围棋赶上韩国,也是在训练量和布局研究这两方面实现了提升。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是迷你中国流开始盛行的时候,但这方面中日韩三国棋手都有功劳,韩国棋手主要是研究了星位的变化。(当然韩国棋手在小目的变化上也有创新,参见刘昌赫对赵治勋的某盘“中刀名局”。)现在我们都知道星位小飞守角后二路跳把角部实地守住很大,据俞斌说这就是李昌镐最先意识到的。俞斌讲,90年左右他去韩国访问,和刘昌赫下棋,刘昌赫就下了这个二路跳,他当时没见过,以为里面还有棋,就试着点进去,结果被净吃了,而这当时在韩国已经是常识了。我们在对局中经常看见放点入的棋子渡过,那不是因为吃不掉,而是吃掉了会被弃子封外势。
当时日本的最强者小林光一喜欢下星加无忧角的新小林流,因此很多比赛形成了新小林流对二连星的布局。白棋的下一手一般都是拆在黑棋的无忧角这边,有拆在星下和多拆一路两种。最开始拆在星下多,认为多拆一路不好,因为黑棋内挂时若尖顶则黑棋在白阵中拆二,若一间夹那么黑棋点角后白棋成为外势加拆二的凝形。只有李昌镐独树一帜,经常在一间夹取外势后悠闲地拆二。他认为黑棋一子有活力,拆大了有破绽,所以只拆二并不是凝形,是积蓄力量的好手。俞斌也讲了这一点,我当年也对这个拆二印象很深,因为这确实违反了经典的日本理论。由于李昌镐对这一拆二的重新评价,对新小林流多拆一路也得到了重新评价,后来渐渐地拆星下几乎绝迹了,都是多拆一路了。
不管是白棋拆在哪里,接下来黑棋外挂后白棋怎么走都是个问题。韩国棋手对这个情况下白棋的走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特别是两个定式,一个是压虎,第二个是守角后黑棋飞角,白棋碰。这两个下法如前面所说都是老变化,都不是韩国棋手发明的,但是韩国棋手发扬光大的。特别是后面的碰,甚至被称为韩国流定式,因为是韩国棋手使这一碰从另类下法变成流行的普通定式。在这两个定式中李昌镐都有不少新手。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二连星对二连星成为了最流行的布局,韩国棋手对星位的研究就更有用武之地了。这一时期特别流行一间夹,李昌镐就是这个时候用悠闲的拆二改变了棋界的看法。被一间夹时跳起的变化也有发展。这时星位变化最让人震惊的发展是挂后飞角再拆二这一看似完美的形状竟然可以被严厉地冲击,冲击手段是尖顶挂角的一子,不过要和二路点结合使用。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很少看到这一尖顶了。
后来在星位的变化上李昌镐又下出了相当神奇的棋。我们最开始学棋时都学过对挂角不能尖顶,因为这样会给对方立二拆三的好形。高手比赛中也确实很少这么下,坂田荣男在对吴清源的十番棋中这么下过,那是另一边有势力配合并且从结果看来并不好。而李昌镐竟然下出了被教科书彻底否定的尖顶,就是让对方立二拆三。接下来李昌镐是怎么继续的呢?是打入后再扳粘,既取地又给对手留下缺陷。要是几十年前的日本棋手穿越到现在看到这样的棋会惊得晕倒吧。不知道是谁发明了这种奇特下法,反正自从李昌镐这样下之后各种尖顶给对方立二拆三就成了一种可行的下法,因为棋手才意识到立二拆三其实也没那么厚。
插个无关话题,这几年对星位挂角,二间低夹的下法比较流行,而以前要夹击不是一间夹就是二间高夹。这有几点原因。首先二间高夹那模样的方向就不在夹击这边,要在夹击这边发展模样一般总是一间低夹,但这有两个缺陷:第一,对方跳起之后正好大飞肩冲夹击的一子。第二,就算对方点角,那之后可以肩冲夹击的一子,被肩冲的一方一般是爬了拐,但这就离外势太近,太重复了,二间低夹那间隔就好些。之所以以前没人下二间低夹是因为觉得被双飞燕后不好,但现在大量的研究证明被双飞燕之后还是可战的,所以二间低夹就流行了起来。
当然李昌镐的创新比起吴清源那是小巫见大巫了,李昌镐只是发展了星的变化,而吴清源发展了星和小目的变化。作为番外篇就再讲一下吴清源的贡献。
提到吴清源的创新都会提大雪崩内拐,但对此事的叙述有很多错误,在此澄清一下。大雪崩定式中黑棋内拐时,白棋如果先挡再断,那黑棋可以还原成外拐定式但便宜两目,所以白棋要先断与黑棋打交换后再挡。一般认为吴清源最开始走内拐时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不然,他是为了吃角,先拐可以紧一气,因为当时的配置取外势不利。当时高川格先挡,但吴清源还是照后来的标准定式下的。所以有人说高川格惊慌失措,结果应错崩溃,也是没看棋谱的胡说,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选择。如果说哪里下错了,无非就是先点了一下,让另一边长不再是先手,但这个长本来就是很晚才发明的,在这个长发明之前的定式和高川格实战的唯一区别就是先点一下损失了一个劫材和连环劫的变化,这个损失也没有多大,谈不上崩溃。还原成外拐定式便宜两目可能是藤泽秀行的发明,而那盘棋藤泽秀行的对手正是吴清源。
其实我觉得拿大雪崩内拐当做吴清源创新的代表实在有点……这种定式中的具体新手藤泽秀行、梶原武雄、桥本宇太郎甚至不以创新著称的坂田荣男都有的是。这几位当然很厉害,但在创新方面比吴大师还是有差距。
吴清源的贡献首先在于占角的选点。传统的日本布局,都是先占小目或目外或高目,再守角或挂角,再拆边,再向中腹发展。秀荣开始在不贴目时大量执白走星位,但还是没人执黑走星位。三三更是没人下。是吴清源和木谷实的新布局革命解放了棋手的思想,使三三和星位成为可以的选项。新布局革命之后,星位和小目才成为两大占角选点。而吴清源对星位和小目的变化都有过革命性的的影响。
我们现在看古代的让子棋,就会发现那时对星位小飞挂,最常见的应法是大飞,单关也有,而现在最流行的小飞则根本没有。古人觉得,要下高位就单关,要下低位就拆二,也就是大飞。几百年大家也就这么过来了,没有人觉得有什么问题,直到吴清源发明了小飞的应法。他认为,大飞看似多拉了一路,但空虚,还是小飞坚实。小飞的最直接好处是限制了对方点角后的活动空间,相比大飞相差很大。看看现在棋里对星位小飞挂有多少是小飞应的就知道这一发明是多么重要了。有趣的是,如果把星位落到小目的位置,吴清源的看法就反过来了,他认为无忧角是凝形,小目应该大飞守角。
我们现在看三四十年代的棋谱,就会发现,那时黑小目白小飞挂黑夹击(黑白是为了方便叙述,换做白棋先占角是一样的)之后,白棋总是托角,托了再虎,几乎没有例外。然后黑棋退,于是白棋立下,舒服地安定。但是,只有一个棋手不是退的,就是吴清源,他是扳打取角,放白棋取外势。最开始日本棋手根本没想过可以扳打,都觉得退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觉得黑棋角上就这么一点空,让白棋取外势实在划不来。但是,就如同李昌镐对一间夹后拆二重新评价一样,吴清源独树一帜地认为,黑棋在角上提一子很坚实,而白棋的外势反而有成为孤棋被攻击的危险。日本棋手托虎然后吴清源扳打,这样的对局下了无数盘之后,日本棋手也输了无数盘之后,日本棋手终于认识到,吴先生也许是对的。后来吴清源晚年摆棋时还嘲笑说:他们就会这个托虎,被我一扳打就不会了。五十年代托还有人下,但后来就逐渐绝迹了,尖顶、飞等下法取其而代之了。
如果把占角看做第一手,挂角看做第二手,那么吴清源首先是改变了第一手的下法,小飞应是改变了星位小飞挂的第三手的下法,使托虎绝迹是改变了小目小飞挂夹击的第四手的下法。那些定式新手都不知道第多少手了,相比起来都不值一提了。
至于为什么吴清源可以有这样的创新,参见他本人的自述。
关于定式
不少人对我创造了许多新定式、为围棋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给予很高的评价。(注:武宫正树在《围棋实战研究》中有这样的评论,作为一名经济学学生,我每次想到那段评论都会想到肯尼斯·阿罗。) 对此,我不胜感激。倘若来问我的意见,我会开门见山地告诉诸位:盘角上的定式本来就和没有一样。其证据是,综观一流棋士的对局,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是按书上写的定式下棋的。
角上的定式本来就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四个角在很大程度上被布局与征子所左右。由于棋子的配置关系,往往出现许多一般看来不成立的手段。大体说来,“定式”这一名词本身就不好。既然说是“定式”,就容易被字面的含义所束缚,使人总是想当然地把它奉为固定不变的东西。可以说“走式”本来只是个单纯的“标准”而已,为了向初学者传授时方便才被过分地固定化了。因此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要像奴隶一样被它打上烙印而盲从于它。比起角上的定式,我倒是想把中盘的手筋、终盘的收官中的许多部分叫作“定式”呢。
如果说我真的创造了许多“新定式”的话,那是因为本人对历来的“走式”毫不重视才引起的。在新布局诞生之前,“一占空角、二守或挂、三要开拆”的顺序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因此,当年的定式相当死板的。特别是在师道尊严、不得造次的战前,同一宗门的年轻棋上要想打出新手,必须要有极大的勇气才行。只要未成强手,稍有标新立异就要遭到周围的一阵怒斥:“你小子还没那个份儿来打新手!"所以,那个时代很难出现新的定式。
因我并非大权威的门徒,不受既成观念的束缚,可以自由地思考。我的师傅濑越先生从未搞过全门棋士的研究会。只要我的成绩不下降,师傅不管我下什么样的棋都不责怪。反过来说,我始终只能一个人单独地研究。虽然这种千里走单骑式的方法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的泥潭中去,但毕竟可以自由思考。就这点来说,我的学习环境可谓无比优越、得天独厚。
即使是铭刻棋史的新布局,我与木谷实在摆脱传统布局思维这一点上虽说一致,但出发点仍有不同。本谷实非常重视中腹难以计算的势力,我则主张“将一手棋便守往角的打法省略,那怕只是一手,也要尽早在边上展开”。被称为“新布局之花”的三连星,就是以我首创二连星为根据的。我刚到日本时,人们都遵循本因坊秀策以来的传统观念下棋,黑棋的第一手只局限于投在小目上。但后来我发现秀荣名人曾执白打在星位上,于是我的黑二连星设想便找到了根据。既然执白打星位都成立,那我执黑去打就更无可非议了。我向来是我行我素,对秀哉名人的对局中,也一视同仁地打出了三三、星、天元的布局,这本来并非蓄意向本因坊门的权威挑战,只是觉得可以这样打才毅然打出来的。
可是,遇到难解的定式时,职业棋士也同样容易被定式束缚。如我在“大雪崩”定式中,首次打出向内拐头的新手时,据说在隔壁房间里研究的职业棋士们顿时骚乱起来,纷纷叫嚷:“吴先生搞错定式了!”另外,比如某个旧“定式”,它是一百多年来始终认为黑棋绝对坏、谁也不去打的“定式”。我之所以敢这样打,只因我总不服气、黑棋究竟为什么不好?如今果然风头调转,都认为白棋不好了。虽说此棋形已少有人打了,但从试探起直到得出白棋不好的结论,足足花费了十年的光阴。说实在的,我本人并没有为了打出新手而事先煞费苦心地反复钻研,许多新手都是在对局中灵机一动地想出来的。
目前,在几百种基本定式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与这些定式的变化有关的定式。也许全部加起来早已超过了一千多种。如此浩繁的定式,就是职业棋士也未必全能记得住。更何况业余棋手那种生吞活剥式的死记硬背,不但枯燥无味,而且毫无意义。实许相告,本人不但对定式知之甚少,而且就在知道的几个定式中仍然混杂着许多不解的东西。我觉得一般业余棋手应该把定式只当作一种“标准”,顶多记住五十至六十种基本形也就足够了。而后再靠自己的棋力,全力以赴地去下自己能透彻理解的棋即可。
只有心中没有定式,才能创造定式。只有毫无拘束的天才,才能创造出最伟大的成就。但是在这一个毫无拘束的天才出现后,日本棋手还是自觉不自觉地被既有观念束缚,直到几十年后韩国棋手的崛起才再次改变了围棋。